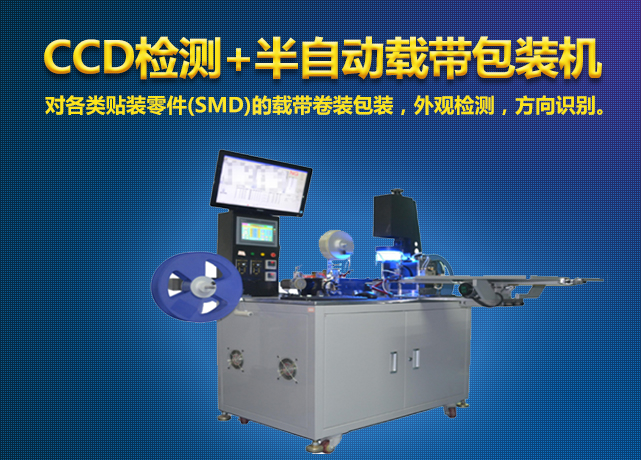杨德昌的电影是国际性的,这从卷帙浩繁的海外研讨文献中不难得出结论。直到今日,关于杨德昌最具价值的研讨著作依然是前法国《电影手册》主编米歇尔·付东的《杨德昌的电影国际》(商务印书馆,2010)以及美国闻名影评人约翰·安德森的《杨德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这两部著作从深度上来说天然无人能及,且都是文本剖析的路子。但美中不足的是,两本书的内容都是从《年月的故事·盼望》开端,并未归入他真实含义上的影视导演处女作——1981年的《浮萍》(米歇尔·付东乃至在只言片语的提及中将本片主演写成了张艾嘉,闹了个大乌龙)。

假如从「杨德昌的电影」这个概念上说,这种挑选倒也无可厚非。但若要研讨杨德昌的整个职业生涯创造,《浮萍》天然是无法绕过的那个真实起点,短少了这部,任何关于这位电影作者的剖析都是不完整的。

这种情况,天然是国外学者对华语电视剧不了解所造成的,再加上画质感人,短少字幕,《浮萍》在国际上的认知度简直为零。即使是在国内,这部隐藏在电视系列剧中的单集也根本少为人知。

《浮萍》是台视公司创造的11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中的一集,该剧由宋存寿、柯一正、刘立立、杨德昌等人每人辅导一集,每集各成单元。
这个系列的推手,是其时如日中天的张艾嘉,她参阅了香港电影新浪潮以电视系列剧培养电影新人的方式(如《七女人》、《狮子山下》和《金刀情侠》),目的以低成本电视制造培养台湾年青创造者的风格技巧。张艾嘉担任制造人,并亲身辅导了其间的第二集《自己的天空》。

杨德昌执导的第四集《浮萍》,叙述一位怀着明星梦的乡村少女来到台北,在大都市里过着浮萍一般的日子,终究愿望幻灭,回归乡土。

以今日的视角来看,《浮萍》逃不开「体裁老套、调度板滞、方法幼嫩,乃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指控,以至于有些观众眼里容不得沙子,给这部著作打出一星两星,或许爽性不供认这是杨德昌的著作。
这种片面的了解,既来自电影史对杨德昌的过度神话,也来自部分观众对台湾电影电视的前史传统缺少了解。

假使知晓1980年代初台湾电视剧全内景程式化的情况,就会知道《十一个女人》这部女人实际体裁剧的开辟含义;假如横向比照《十一个女人》每一集的质量水准,就会知道杨德昌无论如何也是鹤立鸡群——这种亮光,就像他后来的《盼望》在《年月的故事》中那样,是让其他著作相形见绌的存在。

整套剧中《浮萍》的片长最长,到达148分钟(全片可见YouTube台视频道,含两头重复的部分),以至于在播出时分成了上下两集。杨德昌后来的著作简直都拍的很长,此处即见端倪。
这种片长出现的是杨德昌的操控欲和创造野心,《浮萍》尽管是一部托付加工的文学改编著作,但杨德昌坚持依照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拍照,也便是寻求电影化、实景化、戏剧化以及社会图解化。

最典型的便是《浮萍》中出现的三位女人的命运:月花(黯然回乡)、银春(走运嫁人)、莉玲(沦落风尘)。这三位同在台北漂荡的不同年龄段的女人,构成了某种隐秘的年月拼图,宛如那个年代的「20,30,40」(张艾嘉日后或许是从中获得了创意),交织出命运轮回的幻灭感。

同为三女人主角的著作,《浮萍》并不是《月亮星星太阳》(1961/1988)那样的中产阶级类型片,而是严厉扎根乡土,带着一丝健康写实主义的遗风。

此刻杨德昌刚刚回到台湾进入影视业,起步之初天然有仿照的痕迹,但从内核上来说,《浮萍》相同包含着主题和方式上的两层立异,最典型的是他挑选把「问题」和「人物」分隔,只要问题是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

所以不同于张艾嘉,《浮萍》这部著作所言说的要点并非女人,而是遍及的社会问题:永久的城乡二元敌对,以及对表象式日子的批评。
乃至咱们咱们能够说《浮萍》现已包含了1980年代台湾电影的一些重要主题:城乡问题、台北问题、女人问题、家庭问题。杨德昌的著作关乎问题,也相同是关乎道德,才为他赢得电影社会学家的称谓。

受制于故事资料、制造班底、播出前言和经历匮乏的诸多方面,《浮萍》难免有分镜编排上无能为力的当地,最典型的是一些局面的出现单调、编排僵硬乃至是转场时的失焦,但在技能层面,杨德昌依然有不少亮眼的体现。尤其是本集片头从九份山城拍照的几个美丽横摇镜头,让看过《悲情城市》的观众都难免觉察到某种了解的类似感。

况且这种调度上的绰绰有余更多是经费的原因,在杨德昌的职业生涯中更是仅此一例。到1982年的《盼望》,影片分镜编排及全体节奏都充溢光荣。

从全体上来看,《浮萍》和《盼望》(乃至能够包含《海滩的一天》)都是指向女人生长问题,归于某种方式上的「散文印象」,但这些著作所包含的种种隐喻,却现已在渐渐孵化杨德昌后期电影的出题——也便是对社会问题的图解化。

为此,杨德昌的著作必定是遍及说教的,由于言语能够直面问题;他的著作也是高戏剧性的,由于撕裂才干洞穿本相。
《浮萍》的明显指涉,面向都市重复的圈套、女人重演的悲惨剧、山城海滨生机人生的消逝以及愿望的幻灭。这种说教式的指涉乃至以台词方式出现出来:台北是最简单让人习气的,但越简单习气的东西往往是最可怕的。

举凡整个华语界,也只要杨德昌能够用高度隐喻性的镜头来平衡这种极强的说教姿势而不致失衡。《浮萍》中那些缄默沉静的镜头:九份的山城步道以及海滨的岩石孔洞,以一种神秘性的气味将影片延伸到荧幕之外——那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途以及伤痕累累的心灵。

正因如此,将《浮萍》了解成一个细琐往常的女人故事,的确是对杨德昌的一种误读。咱们更应该将《浮萍》视作一个冰山,它浮出的一角之下,是杨德昌的全体社会视界的雏形,的确有某种早熟的预兆。这种早熟,比之侯孝贤在《风归来的人》时分的忽然蜕变,显得更为天分异禀。

所以看完《浮萍》再去看《盼望》,当年的「横空出世」也就变得水到渠成,有了自主出题的权力再加上杜可风等摄影师的支撑。杨德昌的镜头画面就会当即有质的腾跃。

但杨德昌电影的精华始终是在主题方面,也便是交融国学儒家文化、西方戏剧性以及社会图解化(能够视为某种漫画格或许电路图)的有机组成,以电影为手法强力介入社会。这一点直到《》(那个相片墙便是一种图解)初成规划并在《独立年代》中功德圆满。

《浮萍》这样的前期著作尽管从深度到方式都无法与后期著作混为一谈,但它却宛如一个初始凿痕,能让咱们管窥到其创造序列中的中心头绪。
- 上一篇: 沉潜阅读丰盈精神世界
- 下一篇: 網路文學擁抱中華優秀傳統文明

 热线电话:
热线电话: